816 希特勒的賓客簿:二戰時期駐德外交官的權謀算計與詭譎的國際情勢
野獸按:因余杰的書評推介,知道了《希特勒的賓客簿》一書。今天發現楊照也有推介過此書。
绥靖之后,你仍然要面对战争
法国记者让-克里斯多弗·布希萨在俄罗斯联邦军事档案库中找到一份从未曝光的二战历史文件:希特勒的外交宴宾客簿。其中记录着自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参与希特勒生日宴会及其他重要外事活动的外交官的签名。在希特勒自杀身亡之后,大量秘密档案被焚毁,这份登记簿却奇迹般地幸存下来,并成为苏联克格勃“按图索骥”抓捕与纳粹合作过的外交官的证据。斯大林将其据为己有,当做满足其虚荣心的战利品。
斯大林死后,这份文件被封存于克格勃档案库,数十年不见天日。苏联解体后,这批档案开放,布希萨根据这本精美的签名簿,研究若干签名者与第三帝国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本《希特勒的宾客簿》文笔精湛、情节紧凑刺激堪比谍报小说的著作中,布希萨聚焦于柏林总理府酒池肉林、杯觥交错的盛宴,让人宛如置身当时情势诡谲、勾心斗角的外交场合。
签名簿第一页,时间是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日,希特勒五十岁寿宴。六年前,德国人透过民主选举将希特勒送入总理府,相信这个男子会带领德国一洗一战失败的耻辱,开创千年帝国。此刻,五十岁的希特勒活力充沛、精神焕发,在第三帝国宏伟的新总理府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希特勒说:“当这些外交官踏进马赛克大厅,我要他们立即被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强大所震慑。这些长长的走廊,会让我的宾客马上被敬畏之情所淹没。”
大厅中只有大理石,别无长物,占地近一千平方公尺;冰冷如墓穴的大厅里,没有半个家具,没有地毯,没有任何座位,连半张椅子都没有。如此光滑的地面,受邀前来的各国外交官个个如履薄冰。美国大使馆参事派特逊感到自己彷佛踏入一座壮观的埃及法老陵墓:“小国代表恐怕感到大限已近,担忧无法活着离开。”
一九三九年,有多达五十三国在柏林设立大使馆,此数目超过当时世上四分之三的主权国家。从宾客簿中可发现,前来参加盛宴的有来自四十四国的四十八名宾客,阵容庞大。希特勒的朋友真是遍天下——一九三六年冠盖云集的柏林奥运会亦可证实这个事实。
此后,随着战争的爆发,宾客愈来愈少,很多国家成了第三帝国的敌国,外交人员纷纷撤离;很多国家被第三帝国占领,外交人员沦为阶下囚。签名簿最后一页,时间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希特勒五十六岁寿宴。此时离希特勒自杀身亡仅十天,昔日繁华柏林在盟军的轰炸中千疮百孔,总理府只剩下断壁残垣。在这一页上签名的只有三国的五名宾客:日本大使馆参事河原骏一郎、海军武官阿部胜雄及其助理,阿富汗大使纳华兹,及泰国大使朱辛。跟开战前高朋满座、人声鼎沸相比,希特勒已然是众叛亲离、穷途末路,其宴会何等冷清凄凉。
日本是德国的盟友,却承认欧洲已无希望,日本外交官建议德国将残存的潜艇编队移交给日本,以支撑日本在太平洋上继续抵抗美国;阿富汗从德国得到过大笔援助,却没有如约发动对印度的攻击;这些客人中唯一仍然对希特勒忠心耿耿的是朱辛,这位来自泰国的将军比戈林、希姆莱等人还要爱戴希特勒,但他弱小的祖国远在东南亚,根本帮不上忙,他来向希特勒致以最后的敬意。
外交界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出席希特勒生日宴会的嘉宾,不一定全是第三帝国的支持者。他们各有目的,各取所需,有的只是将其当做一项工作,行礼如仪而已。
好几年都出席宴会的中华民国大使陈介,希望维系摇摇欲坠的中德关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从德国获得军备和军事顾问,打造了一支让其他军阀眼红的现代化军队。陈介反对其下属、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向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发放“生命签证”。他竭力讨好纳粹,企图阻止其与满洲国及后来的汪精卫政权建交,但其努力都失败了。弱国的外交不是靠精明能干的外交官就能拯救的。
二十八岁的王替夫是满洲国驻柏林大使馆的一名秘书,因精通德语,被邀请与希特勒共进早餐。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我第一次如此靠近希特勒……,他的双眼流露着他人没有的一些特质,他好像光凭眼神就足以操控我们。”这是很多跟希特勒近距离接触的人共同的回忆,希特勒决不是卓别林扮演的小丑——这种将希特勒喜剧化和妖魔化的方式,无助于理解真实的希特勒。
希特勒召见满洲国外交官,是希望大量进口满洲国的黄豆,黄豆是重要的战略物资。王替夫在出使期间,为逃离德国的犹太人签发了一万两千份签证,但这一善举并未改变他战后的悲惨命运:他被苏联俘虏,在集中营关押了十二年,遣返回中国后,又被判刑二十二年。
爱尔兰是个新兴国家,一九二一年脱离英国统治而独立。爱尔兰驻德大使布利从不掩饰对英国人的深恶痛绝和对德国人的欣赏,他甚至公开支持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其继任者克雷朋更是隐瞒其观察到的犹太屠杀,他只关心过一名被盖世太保逮捕的白俄犹太人雷昂。这种关心跟雷昂本人无关,而是因为雷昂曾是爱尔兰文豪乔伊斯的好友和秘书,藏有一份无价之宝——乔伊斯的手稿。但克雷朋胆小如鼠,不敢出手拯救雷昂,后者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乔伊斯的手稿也下落不明。战后,爱尔兰外长通电嘉奖克雷朋说:“您与夫人经历了一场伟大的冒险。”对比希特勒自杀身亡后,爱尔兰首相公开表达悼念,这样的嘉奖似乎合情合理。
很多拉丁美洲国家的独裁者都将希特勒视为效彷的榜样。在签名簿中,拉美国家使团的签名占据了最大篇幅。这些国家多半是到了战争中后期,才在美国压力之下与德国断交并向德国宣战。但他们始终与纳粹政权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很多纳粹分子在战后将拉美国家当做逃亡目的地。比如,组织和执行“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纳粹军官艾希曼,逃亡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隐姓埋名,在当地的奔驰公司找到一份新工作。拉美国家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多米尼加共和国独裁者特鲁希略对希特勒亦步亦趋,他效彷希特勒的“元首”称号,自我加冕为“恩主”。他派遣其亲信、前记者戴斯帕瑞多出任驻德大使,此人的哥哥是该国外长。这对兄弟得到指示,多明米尼加愿意为犹太人提供十万份签证。特鲁希略打的算盘很简单:他能藉此拯救因屠杀海地黑人而受重创的国际名声,还能为本国引进白人移民开垦原始森林。然而,多米尼加很快就发现无力接纳那么多移民,随即将数字降为五千。一九三九年,开放犹太移民第一年,只有五十名犹太难民抵达这个岛国。总计下来,只有不到一千名犹太人来此碰运气,大部分人后来都逃往美国。
《希特勒的宾客簿》最尖锐的批判,指向那些至今仍保持着欧洲先进国和文明国声誉的中立国——瑞士、瑞典、梵蒂冈。这些国家避开了战争,经济富庶、政治稳定,还表现得特别关心人权、自由、正义等普世价值议题。他们的外交官即便在战火中朝不保夕的柏林,个个都泰山崩而不变色。这些外交官都来自“纯洁无瑕”的国家,那身高雅笔挺的西装上没有沾任何一点血迹,对身边的灾难不必负任何责任——至少他们本人这么相信。真的如此吗?作者像侦探福尔摩斯一样,从草蛇灰线中揭露出这些外交官及其背后的母国,虽号称中立,其实一点不中立。
瑞士大使弗利榭是一位养尊处优的苏黎世人,面对欧洲的独裁政权可说怡然自得。他理解独裁者,也接纳他们时而狂暴的行为。他引用席勒的诗句为自己的态度辩解:“为了不吵醒沉睡的母狮,在骇人的道路上无声前行。”他在回忆录中说,纳粹德国“每个人都安分守己,就像瑞士漂亮牛棚里的乳牛”。自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上任起,他就倾尽全力讨德国欢心,迎合他们的各种欲望。
他做了一件当时没有任何大使敢做的事:建议向德国犹太人施以不平等待遇,唯有德国犹太人必须申请签证才能进入瑞士,其他德国公民可自由进出。他提醒主管部门,必须出手干预瑞士媒体,叫他们别再发表反对希特勒和同情犹太人的文章,“这不仅为了我国的经济利益(德国是瑞士最重要的出口国,也是最大的物资供应国),也是为了瑞士的国土安全着想,因为我国三分之二的国土都与德国为邻”。
瑞士在一九四○年至一九四四年间出口的武器和火药,百分之八十五都送往轴心阵营。德国工程师特别着迷瑞士的钟表工艺,这对德国火炮计划的雷管安置很实用。瑞士的银行为纳粹提供周到的金融服务,帮助纳粹将从占领国掠夺的黄金、古董和艺术品变现,转化成支持战争的经济资源,这种做法才叫“杀人不见血”。
与瑞士一样标榜中立的瑞典,其驻德大使费雪对纳粹百依百顺,丝毫不具备拯救成千上万犹太人的瑞典驻匈牙利特使华伦伯格那样的良知和勇气。德国对苏联开战前夕,像上级命令下属那样对瑞典提出要求:部分德国部队必须取道瑞典领土,前去攻击苏联;德国有权在任何时刻进入瑞典领空,也能在瑞典领海通行无阻,并取得瑞典国家电信网路的使用权。费雪报告外交部,瑞典政府应当满足纳粹的要求,以免重蹈丹麦、挪威被纳粹直接占领的厄运。
瑞典政府犹豫不决,瑞典国王以退位要挟,迫使政府接受德国的要求。为了节省时间,德国军队决定经由瑞典铁路运输,瑞典足足动用了一百零五班列车。瑞典军方高层还发布了一份秘密命令,让自愿参加德军的瑞典官兵更容易实现愿望:“再次呼吁瑞典军士加入东线战场,与德国人协力作战。”费雪在战后因亲纳粹立场被冷冻三年,然后出任北方艾尔夫斯堡省的省长。
梵蒂冈与纳粹政权的隐秘关系,战后受到多方质疑。教宗本笃十二世,经常肯定近在咫尺的意大利法西斯领袖墨索里尼,更将希特勒视为抵抗斯大林的中流砥柱。历史学家康沃尔写了一部名为《希特勒的教宗》的专著,谴责教宗放纵希特勒的暴行,对犹太大屠杀保持沉默,导致悲剧规模不断扩大。
美国研究大屠杀问题的学者祖罗夫也指出:“本笃十二世在当时所有迫害犹太人的地区都驻有外交使节,透过这群外交官,他必然取得最精确的资讯,甚至比盟军更早取得。”梵蒂冈驻德国大使奥萨戈尼是这批使节中最重要的一位,他坐视犹太人被屠戮也不愿对被纳粹迫害的德国天主教徒施以援手。
德高望重的利希腾格神父一直直言不讳地批评纳粹,被捕后在集中营中备受折磨,两年后死去,教廷对其遭遇不闻不问。德军军官格施坦本对亲卫军屠杀犹太人的暴行忍无可忍,亲身到梵蒂冈驻柏林的使馆诉说真相。但使馆不让他进入,更拒绝听他的证词。他后来控诉说:“耶稣教诲世人,‘你当爱人如己’,如今发生了彻底违背教理的可怕暴行,但连身在德国的教廷大使也不愿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我非常沮丧地离开大使馆,绝望透顶,我没有得到任何帮助或建议。”
一九三三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任命历史学者多德出任驻德大使。多德在柏林亲眼目睹了希特勒的崛起。在德国的第一年,他一再注意到,整个国家的人民众对暴行不以为意,人们对每一个新的压迫性法令和暴力行径都不抗议。多德觉得自己好似走进童话中的黑森林,在那里,所有的是非对错规则完全颠倒。他竭力避免参加纳粹的庆典,包括纽伦堡的纳粹党代会。
他公开说:“与自承杀人的凶手握手,让我觉得很丢脸。”他多次警告,“德国团结的程度前所未见,一百五十万兵员拼命在装备武器和操练战技,而且每天受到灌输,去相信欧陆该臣服于他们脚下”。他写信给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说:“我判断德国当局正为一场欧陆大规模的战争作准备,证据很充足,那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在美国国务院和德国外交部的双重压力之下,一九三七年圣诞节前夕,罗斯福提前免去多德的大使职务,换上一名温和派人物。人们总是不愿倾听先知的忠告,因为这些预言都让人扎心。实行绥靖主义政策的国家,后来都付出沉重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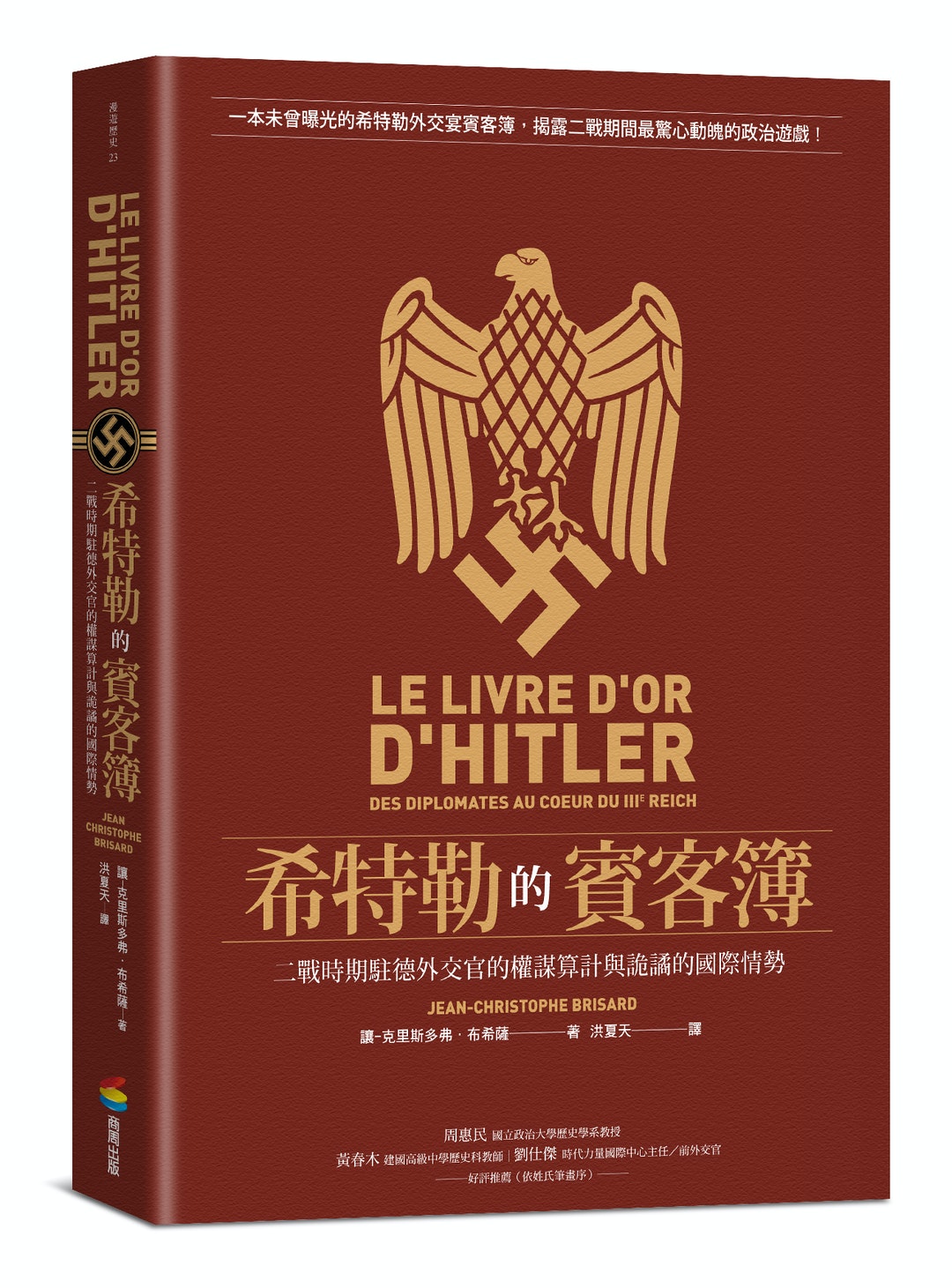
原名:Le livre d’or d’Hitler: Des diplomates au coeur du IIIe Reich
作者: 讓-克里斯多弗.布希薩
譯者: 洪夏天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21/05/08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460元
內容簡介
一本未曾曝光的希特勒外交宴賓客簿,揭露二戰期間最驚心動魄的政治遊戲!
周惠民|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黃春木|建國高級中學歷史科教師
劉仕傑|時代力量國際中心主任/前外交官
――好評推薦(依姓氏筆畫序)
外交宴賓客簿解鎖二次大戰期間歐陸祕史
一個又一個賓客簽名,一項又一項人性與歷史的見證
法國記者讓─克里斯多弗.布希薩在俄羅斯聯邦軍事檔案庫中找到一份從未曝光的二戰歷史文件:希特勒的外交宴賓客簿,其中記錄著自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參與納粹政府重要場合的外交人員與訪客簽名。
隨著希特勒不斷進犯歐洲各國,對德宣戰的國家與日俱增,這些與德意志第三帝國密切往來的人員不僅身處險境,也時時面對著良知的掙扎。他們之中有的同情猶太人,暗中發放簽證,幫忙他們逃往他國;有的深陷希特勒的魅力之中,認為納粹終將攻克眾多敵國;有的表面上雖是中立國身分,私下卻支持納粹,為的是避免祖國落入納粹手中,或唯恐史達林上位毀滅西方文明;有的則落入效忠母國與自身安危的掙扎之中,深怕走錯一步就踏上毀滅之路……
在這本文筆精湛、情節緊湊刺激堪比諜報小說的著作中,布希薩爬梳當時的KGB報告與世界各國外交檔案,透過當局者的視角重現二戰期間諸多事件場景,讓人宛如置身情勢詭譎的第三帝國首都柏林,更道盡當時外交人員的處境,以及參戰各國的爾虞我詐。
好評推薦:
有關希特勒或「第三帝國」的討論已是汗牛充棟,本書作者另闢蹊徑,從俄國軍事檔案庋藏的「第三帝國」禮賓部門舉辦宴會時的賓客簽名簿找出線索,講述一九三九年德國與世界主要國家的關係逐漸發生變化後,各國外交人員的處境,論述或觀察角度都令人耳目一新。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周惠民
二戰結束迄今已七十六年,但近年來相關著作仍紛紛出版,題材更是推陳出新。除了受益於新觀點的解析之外,最重要的還是塵封的檔案文獻陸續浮現,揭開前所未見的歷史現場。
本書主要以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間柏林總理府外交宴會賓客名單的變化,架構德國與各邦交國隨著戰事進行的曲折互動。本書不是小說,但比小說還精采萬分,因為不可能有一位小說家能憑空設想數十個國家駐德外交官在慘烈戰爭和詭譎國際情勢中的權謀盤算,以及各自跌宕起伏的終局。
――建國高級中學歷史科教師 黃春木
如果你對外交官的真實工作面貌有興趣,相信你會喜愛《希特勒的賓客簿》這本書。這本書談的是歷史,也是個人。書中將外交官這份看似高尚的工作除魅化,但同時加上了許多人性血淚。
――時代力量國際中心主任/前外交官 劉仕傑
作者簡介
讓-克里斯多弗.布希薩Jean-Christophe Brisard
法國重要記者,著有眾多深入探討地緣政治的紀實作品,多以獨裁者為主題。他曾與克勞德.凱特爾(Claude Quétel)合著《暴君的子女》(Enfants de dictateurs),近期著作則包括了已被譯為十七種語言的《希特勒之死》(La mort d’Hitler)一書。
譯者簡介
洪夏天
英國劇場工作者與中英法文譯者,熱愛語言文字書籍。譯作:《圖表會說謊》、《被隱形的女性》、《浮華世界》、《用資訊圖表讀懂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為何從眾,何時又不?》、《吸血鬼伯爵德古拉》、《柏拉圖和笛卡兒的日常》、《看漫畫了解人體感官》、《湯姆歷險記》、《天天在家玩創藝》、《騙局》(以上均為商周出版)。
目錄
推薦序 令人耳目一新的二戰史――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周惠民
摧薦序 外交工作的現實與血淚——時代力量國際中心主任/前外交官 劉仕傑
序幕
第一章 猶太人悲歌
第二章 拯救猶太人
第三章 暗殺希特勒
第四章 反抗或低頭?
第五章 藝術與政治
第六章 蘇聯失算
第七章 別有居心
第八章 喪失盟友
第九章 逃離柏林
第十章 真相浮出檯面
第十一章 梵蒂岡的真面目
第十二章 權衡與決斷
第十三章 大限將至
第十四章 最後的宴會
尾聲
簽名簿名單
資料來源
謝辭
序
推薦序 令人耳目一新的二戰史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周惠民
有關希特勒或「第三帝國」的討論已是汗牛充棟,本書作者另闢蹊徑,從俄國軍事檔案庋藏的「第三帝國」禮賓部門舉辦宴會時的賓客簽名簿找出線索,講述一九三九年德國與世界主要國家的關係逐漸發生變化後,各國外交人員的處境,論述或觀察角度都令人耳目一新。
一九四一年底,珍珠港事變爆發,許多國家先是斷交,繼而宣戰。天翻地覆之際,留在柏林的各國外交人員得面臨怎樣的未來?當時,約有一千名駐在柏林的各國外交人員遭軟禁,面臨飢餓與絕望,幽居五個月後才獲准離境,倉皇逃出生天。與之對照的,是一九四五年德國戰敗投降後,與德國尚有邦交的各國外交人員,同樣前途茫茫,只不過,沒有那麼幸運。
一九四四年底,德國敗象已經相當明顯,此時,柏林所剩的使館已經相當有限,但仍努力維持歌舞昇平的假象。一九四五年四月,柏林外交部門終於面對現實,安排各國重要使節撤離,僅剩下一些參事、祕書留守,直到蘇聯軍隊攻陷柏林,將他們俘虜回莫斯科。這種景象,讓人想起金人南下,將北宋靖康之變,兩位亡國之君及皇族、后妃全遭擄往五國城的景象。
提前試閱本書時,許多熟悉的人名、事件出現紙上:滿洲國、大島浩,三國共同防共協定等。本書作者花了許多考證功夫,對「第三帝國」末期與柏林仍保持外交關係的幾個國家:愛爾蘭、日本、滿洲國、泰國的外交官員都有詳盡的考證,也可從他們的遭遇,看盡世情冷暖。
一九三九年歐洲戰事爆發後,除了教廷與永久中立國瑞士之外,瑞典、愛爾蘭也以中立國立場,保持對德邦交,並未撤出德國或其占領區。這些中立國都成為當時兩大陣營的緩衝。瑞士則兩面討好:一方面准許難民猶太通過,另一方面卻接受第三帝國的「納粹黃金」,難怪遭受諸多質疑。一九四三年以後,愛爾蘭駐德大使克雷明(Cornelius Christopher Cremin)與瑞典大使瑞雪特(Arvid Gustaf Richert)在柏林仍相當活躍,參加德國政府舉辦的各種官式活動,在「希特勒的賓客簿」上留下簽名。一九四五年四月,俄軍即將攻入柏林,克雷明已經事先獲得友邦善意警告,立即潛往瑞士,逃過一劫,瑞典大使瑞雪特也於四月二十三日離開柏林,命代辦留守。
相較之下,日本駐德國大使大島浩的境遇完全不同。大島浩是「共同防共協定」的影武者,頗受希特勒信任,日本人甚至稱他為「駐德的德意志大使」,揶揄他的親德立場。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大島浩參加柏林政府的官式活動時,還誓言與德國共赴「國難」。但幾天之後,大島浩便與日本使館許多人員逃往奧地利巴特加斯泰因(Bad Gastein)。五月八日德國投降,美軍抵達,率先管收日本使館人員,將一干人等送到美國審訊,再遣返日本。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大島浩因戰罪而遭起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其終身監禁。在服刑十年後,獲得假釋,隱居東京附近,度過餘生。奉命留守柏林的日本使館參事河原駿一郎則與其他國家使館留守人員遭遇相同的命運:送往莫斯科,而後不知所終。
日本人早於一九三二年成立魁儡政權「滿洲國」,但德國遲至一九三八年才在日本堅持下,給予承認並建交。日本隨即以呂宜文出任滿洲國駐德公使,王替夫則擔任參事。德國投降之前,呂宜文已經先安排其奧地利籍情婦並同兩子返回奧地利,自己則回到「新京」,一九四五年八月,滿洲國瓦解,呂宜文被逮補,曾經遭雲南省高等法院判處死刑,但最終獲赦。留守柏林的秘書王替夫則遭蘇聯逮捕,先在俄國戰犯集中營中服刑十二年,假釋後遣返回國,再度勞改二十二年。一生悽苦,正是蘇武故事的翻版。
作者行文之際,為加強張力,不時加入一些個人想像,例如描寫中華民國陳介大使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參加希特勒生日宴會時,無法順利出示邀請卡的窘狀,又指出「滿洲國」公使呂宜文不通德文。須知呂宜文是日本早稻田大學工學部畢業,當時日本大學中德文不僅是必修,且必須具備相當能力。呂宜文在柏林期間,與其奧地利管家產生情愫,生育子女,說他不通德語,恐怕無法說服讀者。
希特勒主導的「第三帝國」覆亡超過四分之三個世紀,有關「第三帝國」的論述主題甚多,從戰爭破壞文明、猶太滅絕離散到戰後世界重整,率皆有之。從俄軍收繳的「第三帝國」政府文書,挑選宴客的紀錄做為切入點,倒是非常新的嘗試。視角不一,但幾乎可以得到相同的結論:兵,凶器;戰,危事也。
推薦序 外交工作的現實與血淚
——時代力量國際中心主任/前外交官 劉仕傑
外交官的工作,總讓人聯想到光鮮亮麗的一面。一般人談到外交官或大使,總想到出入各大宴會,杯觥交錯的愉悅畫面,例如一個大使代表母國,意氣風發地跟駐在國進行各項談判交涉。
但,你有沒有想過,如果一個大使所派駐的國家,不是正義的一方呢?作為外交官,一方面得聯繫當地的政要,培養與當地政界的關係,一方面又擔心自己未來將被歷史唾棄,甚至影響身家性命,面對這樣的兩難,該怎麼辦呢?
《希特勒的賓客簿》正是一本精彩的好書。時間設定在二次大戰,世界分成同盟國及軸心國兩大陣營,希特勒掌權下的納粹德國當時被認為是歐洲強國。二戰情勢未卜,希特勒橫掃全歐洲,如果你是被派駐在德國的外交官,你又如何預知希特勒終將戰敗?
這本書的標題乍看之下令人有點困惑,為何要談賓客簿?賓客簿有沒有簽到,很重要嗎?但一讀之下,才赫然明瞭,原來本書講的是「作為派駐納粹德國的外交官,該如何在正義良心與捍衛國家利益之間求取平衡?」,以及出席希特勒壽宴或相關納粹德國慶典的各國使節,在賓客簿上寫下自己的名字,等到日後德國戰敗,蘇聯的反間情報組織如何找出這些賓客簿上的名字,並一一復仇的故事。
回想起來,一九三○到一九四○年代的駐德外交官,想必經歷了內心反覆痛苦的糾結。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日,希特勒舉辦五十歲壽宴,這可是一件大事,作為外交使節既然受邀,能不出席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德國「水晶之夜」悲劇震撼全世界,無數名猶太人遭到納粹迫害,但派駐德國的外交官,又有何選擇呢?
書中特別寫到了美國駐柏林代辦當時向德國猶太人核發將近七萬份簽證,讓猶太人得以逃到美國。當時美國第一夫人認為應該要每年准許一萬名猶太孩童前往美國,但這項作法當時並未得到美國國內主流民意的支持,最後美國國會只好作罷。這段故事讓我想到,當時中華民國駐維也納總領事館的何鳳山總領事,也不顧上司駐德大使陳介的反對,執意核發了數千份生命簽證予猶太人,多年後何鳳山被稱為「中國的辛德勒」並獲以色列政府頒贈「國際義人」獎項。書中花了一些篇章提到當時滿洲國駐德大使館也核發了數萬名簽證給猶太人,對台灣讀者來說,這是少見談論滿洲國政府的歷史角度。
這些故事,其實都是在談外交官在歷史的洪流下,如何面對自己的良心,做出最終的選擇。而當時各國在思考是否接受猶太難民的難題時,也深怕難民之中是否曾有納粹間諜。這樣的顧慮是否似曾相識?沒錯,香港自從爆發反送中以來,台灣政府及社會內部激烈辯論是否針接收大規模香港難民,反對派的顧慮即包括:如果這些香港難民中藏有中共間諜呢?
回到一九三○~一九四○年代的納粹德國,當時部分歐洲中立國(如瑞士)或小國的駐德代表,事實上因為忌憚希特勒最終將侵略自己母國,所以在與納粹政府互動時,或多或少帶有一種釋出善意甚至祈求輸誠的卑微心態。是的,外交官不總是光鮮亮麗,有些時候為了保存國家生存利益,總得認清形勢比人強的國際現實,畢竟當時的納粹德國,可是勢如破竹呢!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希特勒意外逃過一場暗殺行動,當時納粹政府急忙召開一場邀請各國使節的公開活動,慶祝希特勒得到上天的眷顧。所有的外交使節都出席了這場慶祝活動,為何?因為作為派駐德國的外交使節,如果不出席這場活動,可能被解讀為不支持納粹德國政府領袖希特勒。作為外交官,必須要在形式上與派駐國廣結善緣,不是嗎?
總之,如果你對外交官的真實工作面貌有興趣,相信你會喜愛《希特勒的賓客簿》這本書。這本書談的是歷史,也是個人。書中將外交官這份看似高尚的工作除魅化,但同時加上了許多人性血淚。
讀完此書,你還會認為外交官出席宴會是件輕鬆愉快的事嗎?也許有時是吧,但更多時候可是戰戰兢兢,苦酒滿杯呢。
書摘
他們說他們沒有選擇餘地。
他們說當時還沒開戰。
他們說當時他們並不知道⋯⋯
那一天是希特勒五十歲壽宴。五十歲是重要的一年,是個逢十整數,恰好半百。希特勒會活到一百歲嗎?他是否真有不死之身?一九三九年的德國,想必有人如此殷切期盼。這是轉折性的一年,值得慶賀的一年,世界還沒因戰爭而天翻地覆。幾個月後,當德國人回想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日這一天,心頭必定會湧起一股懷念之情。這是個天真爛漫的年代,人們無所顧忌地伸直手臂,朝前方高舉過肩,不用擔心受到世人批判。人們也能毫不拘束地高喊「希特勒萬歲」。在一九三九年, 何必因加入納粹或熱愛元首而羞愧呢?他為了德國人民付出了那麼多,不是嗎⁈經歷一九一八年災難般的慘敗,德國終於再次揚眉吐氣。不管是在綠意盎然的鄉間,還是人人辛勤勞動的大城市,希望都再次降臨。失業率、惡性通貨膨脹、共產黨和他們紅色的黨旗,全都消失了,被趕走了,煙消雲散了。它們去了哪兒?那些共產黨人又被送去哪裡?難不成被送到蘇聯去了?不!沒那麼遠。被送到集中營嗎?可能吧⋯⋯但誰會關心那些事?
當然,世事並非完美無憾。人民的飲食品質大不如前,都是因為最近推動的糧食限制。肉類稀少,奶油也很少見。然而為了刺激國家經濟再次蓬勃發展,重建令人驕傲的國軍部隊, 人民盡一點心力也是應該的,不是嗎?就像戈林(Göring)元帥說的:「槍炮與奶油之間,我們已做出選擇!」雖說提倡民族社會主義的納粹黨也難免出現幾個害群之馬,有時惡作劇地嚇唬那些路上的好人,不只是猶太人,他們也會找善良德國人的麻煩。真是太可惡了!要是希特勒知道這回事,他一定會力行改革,晚上的酒館裡,人們低聲地彼此安慰。猶太人?啊, 是的,猶太人⋯⋯他們吃了不少苦頭。但又能怎麼辦呢?種族迫害,暴力凌虐,反猶太法令⋯⋯太可怕了。可怕到連國際社會都關注起這個問題。
一九三八年七月,多達三十二國的代表聚集在利曼湖畔(Leman)美麗迷人的法國村莊埃維揚(Évian)。這是美國總統羅斯福(Roosevelt)的主意。第三帝國再也不想見到那些數以千萬計、百萬計的男女老幼,必須想辦法安置他們才行。國際聯盟(Société des Nations,法文簡稱SDN)的總部設於瑞士, 這場會議自然該辦在瑞士。雖然十分遺憾,但此舉萬萬不可。太複雜,太過耗時了,但最重要的是,向來愛好和平的赫爾維蒂聯邦(nation helvète)何必冒險激怒衝動暴躁的鄰居納粹德國?於是愛充好漢的法國接下這個任務。柏林未受邀請,而羅馬拒絕出席。幾個民主大國才不需要那兩個逐漸朝法西斯主義靠攏的國家加入,一起商討如何處置這些「政治難民」。這些人是「難民」,而不是「猶太人」。後者隱含某種意涵,還是別用的好。在埃維揚,沒有半個人吐出「猶太人」三個字過。他們估量,實在沒必要譴責德國當局。經過一整週的研商,國際聯盟終於達成共識,那就是什麼也不做。沒有人願意改變平時的難民配額。只有一國例外:多明尼加共和國。這個位在加勒比海的國家願意提供十萬個簽證名額,令眾人大吃一驚。但附加條件是他們必須移居到深山叢林的無人地區,開墾拓荒, 推動農業。
埃維揚會議後幾個月,德國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再次爆發一波反猶太迫害行動,激烈的程度可說前所未見。將近一百萬名民族社會主義分子組成的準軍事部隊在一夜之間將兩百六十七間猶太教堂化為灰燼,洗劫、破壞多達七千五百間猶太商店。數十人不幸喪命。歷史稱這一夜為「水晶之夜」。詭異的是,到了一九三九年四月,德國再也沒有人提起這件事,好似這場殘暴無情的暴動未曾發生。只有德國猶太人沒有忘記。他們意識到自己已不再被當人看。不只如此,每個月都有新法令提醒他們這回事。一九三九年春初,新頒布的法令禁止猶太人駕駛任何車輛,除了不能從事醫療、法律業,也不能在任何公共部門任職之外,又再加上了更多職業限制。猶太人別無選擇,只能勉強在沉默中生存。這下德國警察終於放下心來,猶太人絕沒有任何機會破壞希特勒的誕辰慶典。不管是猶太人還是任何人都無權掃大家的興。但誰會想掃興呢?有誰不支持元首?整個德國─或者說幾乎整個德國─都恨不得向他致上最高敬意,展現對他的愛戴。德國在六年前透過民主途徑證明對他的敬愛,甚至為了維護國內和平,不惜擁抱他的專制與暴力。德國相信這個充滿活力的男子會開創一個帝國。五十歲的他看起來正值壯年,依舊活力充沛,精神煥然。這位傑出的政治家深諳如何在歐洲發揮無人可擋的影響力,就連在全球舞台也大放異采。就官方而言,一九三九年有多達五十三國在德國首都設立大使館。此數目超過世上四分之三的主權國家。
但接下來不出五年,將近一半的大使館都會關門大吉。各國大使和外交人員不是回到本國,就是被稱為蓋世太保(Gestapo)的德國祕密警察軟禁。有些人不只失去外交身分, 也失去了國家,遭德國及其盟國併吞。不過我們別太心急。
柏林在一九三○年代末,再次成為放眼世界的外交重地。全球各國都急著派外交官前往柏林。不只美國、蘇聯、歐洲各國,就連拉丁美洲國家和大部分的亞洲國家也是如此,別忘了還有非洲和中東少數幾個獨立國家。不管納粹的政治謀略多麼殘暴,多令人不齒,德國仍是個值得往來的國家。當德國外交部邀請各國外交官前來慶賀元首誕辰,他們都唯命是從。有些國家特別愛挑剔,藉由暫時召回自家大使表達不滿,只留一名代辦或次級官員在柏林。美國、英國和法國選擇這麼做。對美國而言,水晶之夜太過殘暴。英法兩國則是為了強調自己絕非膽小之徒。原本他們對德國的行徑不置一詞,直到一九三九年三月,德國出兵攻擊他們的盟友捷克斯洛伐克。根據德、法、英、義四國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簽下的協約, 只要蘇台德地區納入第三帝國的領土,希特勒就保證不會向那些中歐的鄰居小國下手。有誰真相信納粹的保證呢?捷克人絕不會相信。
他們是對的。
簽下慕尼黑協定後不到六個月,德軍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浩浩蕩蕩進入布拉格。德軍的藉口─當然得找個藉口才行─看似十分單純,甚至稱得上慷慨大方:斯洛伐克渴望獨立,好心的德國只想保護他們。隔天希特勒就立法明定在捷克成立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保護國,將之併入德意志第三帝國版圖。斯洛伐克則宣布獨立並自願接受德國保護。
羅伯.考朗德(Robert Coulondre)自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開始擔任法國駐柏林大使。在此之前他已在莫斯科擔任過兩年的駐蘇大使。他對獨裁者並不陌生。然而這一回希特勒藉由攻擊捷克斯洛伐克,展現武力強權,格外讓他怒不可遏。他一聽說這件事,立刻提筆向位在巴黎奧賽堤岸的法國外交部報告。「德國這次的舉動,再次證明他們對所有書面承諾不屑一顧,寧願訴諸殘暴武力,先下手為強,使之成為既定事實再說,」他向上級呈報,「德國的行動撕毀了慕尼黑條約⋯⋯再次證明德國政治毫無原則,只遵從獨裁者的命令:伺機以待, 一旦找到有利時機,立刻掠奪雙手可及的所有戰利品。這簡直是強盜幫派和叢林野人之流的價值觀⋯⋯」
英國大使韓德森(Henderson)則更進一步,主張與德國斷交。考朗德反對這麼做。他傾向採取沒那麼決絕的作法。「最重要的是,」他後來在回憶錄中描述,「一方面組織集結愛好和平的國家;另一方面,無需大張旗鼓,但必須以堅定的態度,讓希特勒明白自己的征服大計已被圍堵。」具體而言,就是倫敦和巴黎不約而同召回駐德大使,只為了讓他們「回本國報告」。考朗德於三月十九日離開柏林,直到四月二十六日才抵達巴黎。英法兩國的行動是否真讓納粹印象深刻?希特勒的壽宴是否因此黯淡了幾分?考朗德暫別柏林、前往巴黎的前一晚,遇到戈培爾麾下的一名中尉,對方開誠布公地說道:「各種機會攤在我們面前,那麼多的門都為我們敞開,我們忙得真不知如何是好呢。」
就這樣,考朗德缺席了希特勒的五十歲壽宴。總理府簽名簿上,代表法國出席的是克里斯蒂安.卡何.德.沃聖錫爾, 一位曾出使哈瓦那的外交官。在他的簽名下方不遠處,則是美國代辦雷蒙.蓋斯特的簽名。蓋斯特不喜歡納粹,但他對他們頗為熟悉。他時常與親衛隊兩名領導人希姆萊(Himmler)和海德里希(Heydrich)會面。這些往來足以讓他明白,德國猶太人的下場恐怕不妙。希特勒生日十五天前,一九三九年四月四日,蓋斯特向美國助理國務卿喬治.梅瑟史密斯(George Messersmith)上呈一封機密文件,內容令人驚慌失色。「猶太人的問題,只能在德國境內解決,而我認為他們(負責的納粹官員)準備用他們的方式處理這個難題。也就是說,他們肯定會將所有健全的猶太人送進勞改營,將所有猶太人的財物全部充公,隔離猶太人,對猶太人社群施以更高壓的措施,接著以武力解決大量猶太人。」這話說得再明白不過。
在此背景下,蓋斯特和駐柏林美國領事館的同仁,於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九年間向德國猶太人核發了將近七萬份簽證。這數字令人肅然起敬。但事實上他們原本可以核發更多簽證,加倍甚至再加倍。在此期間,美國當局原本願意迎接超過十八萬四千名德國移民。可惜的是,美國駐柏林領事館的工作量太過繁重且人手不足,以致最終核發的簽證數量有限。但這只是部分原因,事實上另有隱情。實發簽證遠低於官方額度的主因,其實是試圖前往美國的申請人財務狀況未達要求。他們太窮了。美國剛揮別始於一九二九年的經濟大蕭條,無意迎來成千上萬的貧苦人家。即使那些人可能會就此喪命。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展現決心,堅持全面拒絕「可能會成為全民負擔」的簽證申請人。然而,納粹很快就禁止猶太人帶著身家財產離境─如果他們還有財產的話。自此之後,渴望離開德國的申請人要是在美國沒有親戚能照顧他們,就會被拒絕入境。但這只是第一道障礙而已,他們還遭遇其他困難,一個更加陰險的阻礙:美國幻想希特勒也有「第五縱隊」(Fifth column),也就是難民之中可能藏了納粹間諜。
連孩童也無法擺脫這種疑慮。水晶之夜爆發後,美國第一夫人愛蓮娜.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決心全力推動新法令,希望在未來兩年間,每年特許一萬名德國孩童前往美國。對象是不滿十四歲的小孩,也就是原則上無害的人選。但美國民眾可不這麼想,此計畫引起激烈反彈。一九三九年初,新聞媒體發表一項民意調查結果,當民眾被問及:「有人提議每年接納一萬名德國難民兒童─其中大部分都是猶太人─並把他們交由美國家庭照顧。你認為政府該不該讓這些孩童到美國來?」高達百分之六十一的受訪民眾對此說「不」,只有百分之三十的民眾同意,另有百分之九表示「沒有意見」。接下來的其他民調也出現類似結果。連美國菁英階級都反對接納這些年幼難民。羅斯福的表親,羅拉.德拉諾.胡戴林(Laura Delano Houghteling)是美國移民局局長夫人,她宣稱:「兩萬名可愛孩童不消多久必會變成惹人厭的貧窮大人。」面對如此激烈的反對聲浪,國會只好放棄此計畫。
納粹持續迫害德國猶太人,但人們拒絕向他們伸出援手。那些在柏林的外交官是否聊起過這回事?美國代辦是否曾向同行提起,排在領事館門口的猶太人一天比一天多?想必他不會跟瑞士大使弗利榭說這回事。他絕對不會沒發現弗利榭絞盡腦汁只想避免激怒納粹。他深恐自己的國家會踏上奧地利和捷克地區的後塵,被德國巨獸一口併吞。赫爾維蒂聯邦境內有一大塊區域都以德文為母語,不是嗎?希特勒很有可能會宣稱,瑞士必須加入大日耳曼帝國。弗利榭不斷提醒、警告自家政府,瑞士身處千真萬確的危險之中,絶不能貿然與強大的日耳曼尼亞起衝突。自他於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上任起,就傾盡全力討德國當局歡心,迎合他們的各種欲望。即使再誇張的要求,他也一口答應。因此他做了一件當時還沒有任何大使敢做的事:建議向德國猶太人施以不平等待遇。唯有德國猶太人必須申請簽證才能進入瑞士領土,其他德國公民依舊可以自由進出。弗利榭認為自己是為了瑞士著想,才向第三帝國如此輸誠。不然的話呢?正如他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呈交上級伯恩的文件中提到,若要求所有德國公民都需要簽證才能入境, 可能會讓柏林認為「瑞士不友善,甚至違反中立原則。」
德國政府接受了弗利榭的提議,不過有個條件:秉持互惠原則,他們也會對前往德國的瑞士猶太人施加同樣的不平等待遇。為了一眼就能辨別瑞士人,納粹進一步建議在猶太人護照的第一頁左上角做記號,以一個圈起來的J當作識別符號。柏林瑞士大使館的代辦法蘭茲.卡普勒(Franz Kappeler)附和納粹的提議,並告知瑞士外交部:「我認為德國的提議認真考量了我方需求,我們可以接受。」接著他頗為務實地補上一句:「在現今情勢下,相信需要前往德國的瑞士猶太人應該非常之少。」不過瑞士政府最終拒絕了德方請求,沒有在護照加註持有人的猶太血統。不過瑞士還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與柏林簽下協定,要求所有德國猶太人必須申請簽證才能進入瑞士。
赫爾維蒂聯邦雖然是第一個同意區分德國非猶太人與猶太人,對後者施加不平等待遇的中立國,但瑞典很快就跟進。幾天之後,瑞典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與德國簽定類似的協定。其他歐洲國家開始考慮歧視猶太人方案可不可行。比如荷蘭和愛爾蘭。愛爾蘭駐柏林大使名叫查爾斯.布利(Charles Bewley)。當時的愛爾蘭還是個新興國家,經歷漫長過程終於在一九二一年脫離英國統治,宣布獨立。然而直到一九三三年,愛爾蘭總統才決定不再效忠英格蘭國王。布利一直是愛爾蘭獨立運動的支持者,他從不掩飾自己對英國人的深惡痛絕。他實在太痛恨英國人,甚至轉而欣賞德國人,特別是納粹統治的德國。自一九三三年來到柏林後,嚴厲的外交官很快就顯露他討厭猶太人的本性,甚至公開支持德國對猶太人的政治迫害。就像瑞士與瑞典外交官員一樣,他希望嚴格限制德國猶太人進入他的國家。當他得知都柏林准許九十名「非亞利安血統的基督徒」暫時居留,他怒火攻心。一封標著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發給愛爾蘭外交部的電報中,他明指這些「非亞利安血統的基督徒」,想必會是一群「為了換取利益,不惜接受基督教受洗禮」的猶太人。他冷酷地明列各種理由,陳述為何必須禁止這些移民入境,卻不希望自己被當作反猶太人士:「總結而言,我想再補充一件事:如果人們認為我對那些渴望離開中歐的猶太人毫無同理心,我將會感到十分遺憾。但我深切相信,當猶太人的利益不符合愛爾蘭人民的利益時,基於以上所提的種種因素,我必須像所有相關人士一樣,盡一己責任,拋卻個人同情心,以維護愛爾蘭利益為要務。」戰爭讓愛爾蘭沒有時間決定如何處置這些移民。中歐猶太人很快就失去遷徙移動的權利。
《希特勒的賓客簿》:並不是每個國家都痛恨納粹,美洲有好幾個國家首領都非常景仰元首的魅力
美國人、俄羅斯人和中國人……攤開全球地圖,這三國占地廣大,相比之下版圖狹小的納粹帝國幾乎無足輕重。而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這一天,這三國的共通點是,他們都出兵對抗軸心國。獨立中國最後也向德國和其盟國義大利宣戰。那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轟炸事件隔天。陳介事先警告過魏茨澤克,中國人很有耐性,但觀察力也很敏銳。前大使是否還掛念著他的同伴,那些留在柏林的各國外交官?此刻他人在紐約,在美國新朋友的簇擁下歡慶新年。德國有多少人暗暗羨慕他?
德國首都如今變得陰沉可怕,好像老披著一層送葬面紗。沒向軍隊或親衛隊報到的德國人,全都在工廠裡日夜趕工,直到筋疲力盡。男性勞動力不足,德國轉而徵調全國婦女,只有家有幼童的人逃過一劫。全國工人不分男女都必須增加勞動量。每天工作超過十二小時是家常便飯。未經政府核准,不得任意變換工作。只要在工作場所違反任何規定,就會遭到嚴厲懲罰,甚至被關進集中營。根據民族社會主義原則,每一個公民都屬於國家。國家強大就能保護人民,而人民必須為此犧牲一切,首當其衝就是自由。
戰爭迫使政府頒定愈來愈多的限制。全國產業體系都用來支持軍事需求,製造武器、鍋具、制服、軍靴、糧食……也就是進攻歐洲和其他地區的德國軍隊所需要的一切物資。人民也必須學會挨餓。他們不會抱怨,不敢抱怨,他們選擇了希特勒,希特勒是他們的共識。然而各國外交官的看法與人民大不相同。
墨西哥代辦納巴若於一九四○年三月上任。他受夠了。他苦悶地表示他們什麼都缺。「蛋成了非常珍貴的物資,一週只能領一顆。奶油和食用油也都成了奢侈品,政府一個月只配給五百克。」值得慶幸的是他很快就會離開柏林。他一拿到出境簽證就能回家鄉。墨西哥政府已於十二月十二日與德國斷交。好極了。墨西哥外交官再也受不了妄自尊大的納粹和他們的暴行。
斷交前一個月,他和南美洲各國代表在十一月齊聲要求德國政府別再在法國處決人質。這讓他們惹了大麻煩。德國人非常惱火,要求他們和其他使節一樣乖乖聽話,當個稱職的配角。第三帝國要殺誰就殺誰,想何時動手就動手。納巴若還記得接下來幾天,墨西哥使館的信件被德國情報人員明目張膽地攔截。「這使我不得不向柏林的外交部寄出一封言詞激烈的抗議書。我隨信附上那些信封,雖然墨方加以密封並印上火漆,但仍被德國情報人員拆開。」德國官員的回覆令他啞口無言:「他們只以口頭向我解釋,那是因為信封上的地址不清不楚,審查人員才會犯了點小失誤。」
令人意外的是,一九四二年的新年宴會進行得非常順利。迎賓人員欣喜地指出,並非所有美洲國家都背棄了德國首都。德國的「朋友」,那些繼續公開支持希特勒執政風格的國家都派了很多官員出席。宴會廳裡,光是阿根廷人、玻利維亞人和巴西人就占了一大半。其他國家則持保留態度,行事比較謹慎,甚至有點坐立難安。烏拉圭、巴拉圭、厄瓜多……全都只有寥寥幾人出席。不用懷疑,他們接下來會一一背棄德國。
還有些根本不該現身的魯莽傢伙,比如委內瑞拉的代辦和尼加拉瓜的代表。他們來帝國總理府幹嘛?他們的政府都已和德國正式斷交。拿委內瑞拉來說,委德兩國前一天才剛斷交,代辦拉斐爾.安格瑞塔.艾爾維洛(Rafael Angarita Arvelo)剛剛卸下職務。至於尼加拉瓜使節托馬斯.弗朗西斯科.梅迪納(Tomas Francisco Medina),他的國家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就向德國宣戰,這之後已經過了整整三週,他竟然還出席官方宴會。
但還不只如此。即使有時差,尼加拉瓜人也不可能不知道自家政府幾個小時後會在紐約做什麼。他們會再一次侮蔑希特勒政權,甚至提出比宣戰更可怕的宣言,他們保證會徹底摧毀、完全殲滅民族社會主義。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的同盟國公開宣言,尼加拉瓜也會參上一腳,誓言對抗軸心國。美、英、蘇、中和另外二十四國,包括尼加拉瓜,一起簽定了《聯合國家宣言》(Déclaration des Nations)。它明白宣示:「每個國家都會盡力投注軍事和經濟層面的所有資源,對抗簽下三方協約的軸心國……絕不能自行與敵國簽下停戰或和平條約。」
當梅迪納在一月二日,通知德國尼加拉瓜簽下《聯合國家宣言》時,德方的反應違背了公平原則(Fair Play)。德國禁止梅迪納離開,將他軟禁在使館內。南美洲其他國家的外交官也都面臨同樣的命運。他們膽敢背棄德國?還妄想離開?把他們全關起來!希特勒下達了命令。沒有他的允許,誰也不能走。這些聽命於華盛頓的奴才!他晚點再來收拾他們,必得讓這些人付出代價不可。一定是猶太人的陰謀。那些該死的「國際猶太社群」想必操縱了這些「墮落的」國家。就連尼加拉瓜共和國也簽了《聯合國家宣言》!為什麼這消息令人如此震驚?這個加勒比海小國,不是從一九三八年起就歡迎德國猶太人移民過去嗎?那是二戰爆發前,埃維揚會議做出的決定。
拉斐爾.楚希約(Rafael Trujillo)不需要希特勒傳授任何獨裁祕技或個人魅力。他也是個受到全民愛戴的一國領袖。他從一九三○年起統治多明尼加共和國,這個以西班牙文為官方語言的國家與海地共享伊斯帕紐拉島(Hispaniola)。楚希約和希特勒的共通點顯而易見。希特勒打算將柏林改名為日耳曼尼亞?楚希約更進一步。多明尼加首都原名為聖多明哥(Saint-Domingue),他藉由賦予其更莊嚴的新名字,反映這座城市所象徵的一切。他把首都改名為楚希約城(Ciudad Trujillo)。
他的出生地聖克里斯托巴(San Cristobal)也一樣,從此以後被稱為楚希約。那多明尼加和加勒比海地區的最高峰杜阿提峰(Pico Duarte)呢?當然改為楚希約峰。當希特勒成為德國人民的「元首」,代表領導之意,楚希約則另創稱號:「恩主」(el Benefactor),意指大恩人。希特勒只是名下士,但楚約希可是最高統帥和海軍司令。前者痛恨猶太人,後者則不。楚希約痛恨的是海地移民。為什麼?原因很簡單,他們是黑人。楚希約希望多明尼加共和國只有白人,像他一樣的白人。其實最好不要完全像他一樣。楚希約的外公是海地人。祖先的血統讓他的皮膚顏色深了些,多了一層晦暗色澤,很容易就被曬黑。惡意攻訐他的人宣稱,楚希約為了遮掩「不純」的血統,會在官方場合使用化妝品讓皮膚變白。不管如何,楚希約認為他的國家接納了太多海地人。那些在蔗田裡揮汗如雨、領著微薄薪資的黑人農工都必須消失才行。一九三七年十月,德國人還沒想出猶太人的「終極解決方案」,他已下令以極端暴力解決海地黑人的問題。把他們全殺了!
當地歷史稱這場大屠殺為「大斬殺」(El Corte)。理由很簡單。多明尼加人手持刀子或長彎刀處刑。政府明令禁止使用槍炮類的武器。這樣才能宣稱那些「入侵」的海地人和多明尼加農民起了爭執,一發不可收拾。楚希約可不希望被國際社會視為殘忍的屠夫。結果十分慘烈,多達一萬人喪命,實際數字甚至可能加倍。至今這場屠殺仍被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場大規模的種族屠殺。
一年之後,埃維揚會議於一九三八年七月召開,世人非常關切德國猶太人的命運。必須想辦法拯救這些人。誰願意接納他們?沒有人出聲。只有楚希約。這下殺人犯成了救世主。他願意為猶太人提供十萬份簽證。他打的算盤很簡單:他不但能藉此重建國際名聲,還能為本國引進白人移民。埃維揚會議後過了五個月,他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派遣羅貝托.戴斯帕瑞多(Roberto Despradel)前往柏林擔任駐德大使。戴斯帕瑞多原是名記者,是楚希約的親信。他的兄弟阿圖羅.戴斯帕瑞多(Arturo Despradel)是外交部長,也是他的直屬上司。猶太人問題就由這一家人全權處理。
諷刺的是,戴斯帕瑞多兄弟毫不掩飾對歐洲專制政權的著迷,熱愛法西斯和民族社會主義。希特勒和楚希約惺惺相惜,前者也派了名大使長駐楚希約城。見證此事的英國代表擔憂地表示,元首試圖「利用多明尼加政權的親納粹和反美立場」。德國海軍對加勒比海島國的海岸線特別感興趣。多明尼加擁有眾多深水港,萬一德國與美國開戰,這些情報可能會帶來不少優勢。除此之外,還有不少關於納粹間諜的流言。他們可能已與多明尼加政權打上交道。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三年過去了。羅貝托準備告別柏林。他的兄弟阿圖羅要他關閉使館並打包回國。多明尼加共和國選擇美國陣營,向德國宣戰,令眾人吃了一驚。楚希約是名務實的暴君,也是個巧妙的交涉家。他不只說服美國人忘記海地人大屠殺,而且他的加盟還賣了個好價錢。他迫使華盛頓同意提供優惠貸款,供應軍事物資和訓練人員,並在多明尼加境內各處建立空軍基地網。至於發給德國猶太人的十萬份簽證,已被人們拋在腦後。多明尼加很快就發現根本無力接納那麼多移民。政府重新評估後,把數字降為五千人。人在柏林的羅貝托是否達成這個目標?一九三九年,也就是開放猶太移民第一年,只有五十名猶太難民抵達伊斯帕紐拉島。大部分都年老力衰,對農業一竅不通。然而,多明尼加大使早先卻向獨裁者保證會引入雙手長滿繭的健壯農民。這些男男女女會把遭人遺棄的老香蕉園改造成肥沃的農田,就像巴勒斯坦的基布茲(Kibboutz)。
至少,這是楚希特的幻想。按理,猶太移民應在多明尼加北部,索蘇阿(Sosua)附近地區建立一個興旺的殖民群落。那裡是整座島最貧困的地區之一。這項移民計畫在一九四一年告終,因為納粹對猶太人封閉了整個國界。沒人能離開德國。聖多明哥的猶太區早就宣告失敗。人們全都垂頭喪氣。他們之中有音樂家、商販、律師、教授、教士,但沒有半個熟悉農務的人,沒人體驗過這種鄉間生活。炎熱的氣候,貧瘠的土壤,熱帶特有的疾病,全都消磨了他們的意志。總計下來,只有不到一千名猶太人到多明尼加共和國試運氣。留下來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大部分人一有機會就急忙逃往美國。
多明尼加共和國、中國、古巴、瓜地馬拉……這些叛徒全讓瑞士大使弗利榭灰心喪志。一九四二年的新年宴會,他沒有前往總理府。他寧願派代辦卡普勒代表出席。表面上他以健康因素為藉口,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參戰,而且美國要求瑞士擔任美國在德國的委託代表。怎麼做才不會激怒納粹?弗利榭在同意美國的請求前,先見德國官員,要後者放心瑞士絕不會改變中立立場。德國一開始佯裝不悅,其實想趁機交涉新的商貿合約,特別是軍需品的補給。
瑞士在一九四○年至一九四四年間出口的武器和火藥,百分之八十五都送往軸心陣營。德國工程師特別著迷赫爾維蒂聯邦鐘錶工藝。這對德國火炮計畫的雷管安置很實用。弗利榭再次為了滿足德國人的需求,傾盡全力遊說本國政府。千萬別惹德意志帝國生氣,千萬別加入這場世界大戰。他拒絕道德判斷,不願評斷愈漸激進黑暗的德國政治。「雖然這種說法也許有點過時,但中立國絕不能干涉外國政治,」他在戰後所寫的回憶錄中為自己辯護。
但弗利榭幾天後就崩潰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他要求休假。他渴望離開,遠離柏林一觸即發的情勢。「我懇求您准許我於下週回到伯恩,」他向上級表示,「基於健康因素,我必須安排三週假期,之後才能重回崗位。」此刻適合離開德國嗎?他保證。一切都井井有序,瑞士與德國官方的關係從未如此和諧。那些在十二月要求瑞士保護的國家呢?弗利榭的手下處理得非常完美。「已設立特別部門加以處理,運作得十分順利,毫無阻礙……」
就假設而言,瑞士保護的國家名單說不定很有可能在不遠的未來進一步增加。何時?很快就會發生。但弗利榭不想討論這件事。至少不是現在。他的精力有限,請見諒,他必須為自己的健康著想。「即使接下來幾天或數週內,更多的南美洲國家請求我們負責維護他們的在德權益,我也沒有待在柏林的必要……」弗利榭在一月二十九日提出歸國要求,絕不是偶然。里約會議剛於前一天在巴西結束。美洲二十一國的外交部長在美國的牽線下齊聚一堂,開了整整兩週的會。
華盛頓的目標再清楚不過:團結整個美洲的勢力,一同將軸心國置於死地。首先,美國要求出席各國與德國及其盟友斷絕一切外交關係。面對拉丁美洲各國的外交部長,美國副國務卿薩姆納.威爾斯(Sumner Welles)一開始就定下主調:「只要希特勒主義和他那些可怕害蟲沒被徹底消滅,只要軍國主義的日本沒被擊潰,就不可能有和平的一天……他們必須明白他們再也不能任意摧毀世界各地,一代代男男女女的性命。」人們禮貌地舉手鼓掌,但少了幾分熱情,理由很簡單:並不是每個國家都痛恨納粹。何必摧毀希特勒?何必打敗民族社會主義?
美洲有好幾個國家首領都非常景仰元首的魅力。特別是玻利維亞、智利、巴西和阿根廷。要他們背棄第三帝國,美國必須耗費漫長時間多方交涉才行。但威爾斯辦到了。雖然不是全部,但絕大部分的國家都先後與軸心國斷交。烏拉圭和祕魯於一月二十五日宣布,巴西和玻利維亞則在二十八日行動,隔天輪到厄瓜多,三十日則是巴拉圭。只剩下智利和阿根廷仍堅持原本的立場。
德國人嘗到被背叛的苦澀。連玻利維亞都轉身而去。玻利維亞駐柏林大使館的首席祕書菲德利科.尼爾森─雷耶斯(Federico Nielsen-Reyes)不是熱忱地崇拜希特勒嗎?他不是老吹噓自己是第一個把《我的奮鬥》(Mein Kamph)翻成西文並出版的人嗎?那是一九三五年的事。德國的盟友避免不了這波民族社會主義的浪潮,更何況玻利維亞還受數名親納粹的軍事強人統治。
玻利維亞長年來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政變,權力不斷輪替。再加上玻利維亞的日耳曼族群很有影響力,數年來得以替當地與民族社會主義建立密切關係。衝鋒隊原是納粹黨內主要的軍事部隊,殘暴的恩斯特.羅姆(Ernst Röhm)則是衝鋒隊的首腦,但在一九三四年的「長刀之夜」被希特勒剷除勢力。羅姆曾經接受當地高官委託前往玻利維亞,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年間組建並重整軍隊。當時他趁機宣揚希特勒的思想。十年過後,那些曾受羅姆訓練的年輕軍官都成了掌控國家的大人物。既然如此,這些人怎會在一九四二年一月轉頭倒向美國呢?
這全歸功於同盟國的一項祕密行動。一個令人嘆為觀止的巧妙計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