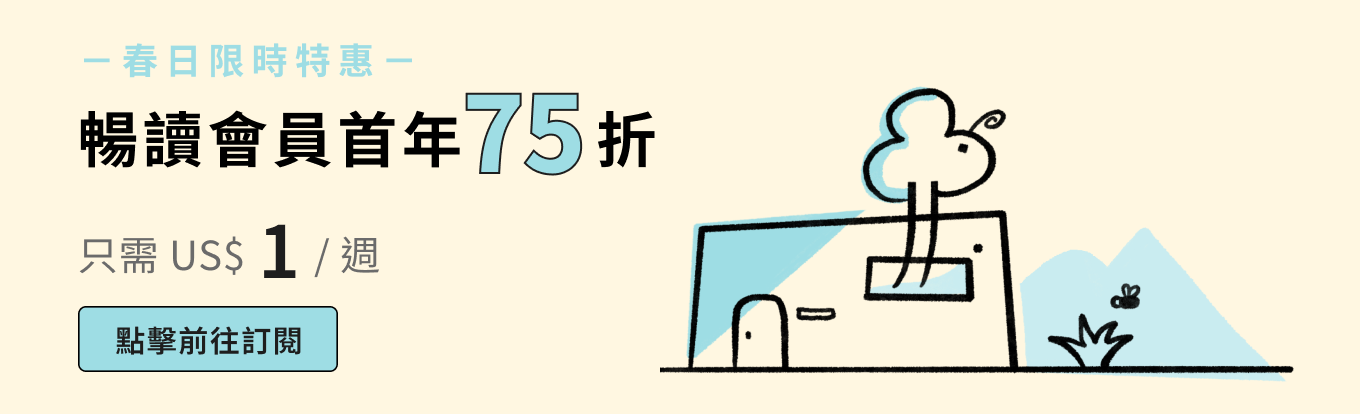张赞波专访:时代中人性越加卑劣,如何记录,如何受伤
“有时看到星空、月亮、晚霞,幸好这些还没有被直播宇宙、被这物欲横流的世界完全污染,这样的部分永远在的。”

为了捕捉日落时分大稻埕最后的光线,这次作为受访者的张赞波,在镜头前站了良久;一直等到机器放下,他才松了一口气,腼腆地说道:“还真不太习惯在镜头前面。”事实上,自从开始拍纪录片,张赞波一直是那个扛著器材到处走、藏身于镜头后面的人。
他的镜头下,有被卫星残骸击碎了日常的中国山村居民(《天降》,2009),也有拦截上访民众的基层官员(《有一种静叫庄严》,2011)。对于大时代里的底层生活状态,张赞波总是能够观察入微。2014年,他以非虚构文学作品《大路:高速中国里的低速人生》获台北国际书展大奖非小说类首奖;而后,与之相应的纪录片《大路朝天》也广受关注,并在电影奖项中收获颇丰。
大路之后,阔别十年。2024年,张赞波终于带来了最新纪实作品《大景:内蒙古“皇家”草原上的奇异风景与欲望游戏》。这本原将由八旗出版的长篇巨著,因总编辑富察在上海失踪而几经延宕,最终由春山接手出版,历经时多番周折后,如今终于到了读者眼前。时隔多年,张赞波也终于随新书发布之际再次到访台湾;与他一起来到我们眼前的,不只是书中喧杂的景区与直播景观,还有因为多年记录、冲撞现实后难免受伤的内心。
张赞波(1973-),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湖南人。200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班,2009年完成纪录长片处女作《天降》。2015年,第四部纪录长片作品《大路朝天》入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获第53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提名。2018年起在内蒙古拍摄,2020年因疫情爆发中断。疫情期间将记录整理成《大景:内蒙古“皇家”草原上的奇异风景与欲望游戏》一书,2024年在台湾出版。
“新闻何为?艺术何为?利用新媒介的这些人,真的是只想吸引流量,而不去承担一点点社会责任。”这片热闹图景的背后,有的并不是言论自由,而是无远弗届的审查与封禁。

直播间里的异域风景
去年年底,上下册如两块厚实砖头的《大景》,出现在各家书店的展示台上。
这是一部篇幅浩瀚的非虚构文学,书写背景设定在2010年代后期,中国各地为发展旅游产业而兴建了许多风景区,同时短视频经济也在冒起,各式各样的影音平台“抖音”、“快手”等,快速吸引了大量用户入驻。2016年才出现的“抖音”平台,官方数据显示两年间就收获了超过五亿的活跃用户,张赞波敏锐捕捉到这一有趣的文化现象。他在平台上追看过卡车司机,也看做手工的人,这类形式“比较独立,在精神上(与纪录片)也有共通之处”,因而吸引到了张赞波的关注。
然而,促使他进一步踏入、乃至记录直播宇宙的契机,是一位化名柳静的直播主,她以在观光景区养狼而得到了百万人关注。
“一位穿著米白色夹克的女子正坐在右边床上刷手机,看到老王和我进来,她抬起头,看了一眼,面无表情⋯⋯”这是柳静在书中的首次出场,自带数位冷漠让读者直打寒颤。然而到了直播间,她完全改换神情,表演人狼大合唱,在数以万计的粉丝眼中成为焦点,还不断有贵重礼物从萤幕上闪现。
现实生活中并不起眼的人,到了直播平台上,摇身成为高流量明星,这正是最初让张赞波感到好奇的现象:“这些直播主很多都是底层人,我就想,一个底层人是如何利用最新的社群媒介、经过怎样的运作,在网路上吸引来这么多人,并且成为一个网红的?”
“这些直播主很多都是底层人,我就想,一个底层人是如何利用最新的社群媒介、经过怎样的运作,在网路上吸引来这么多人,并且成为一个网红的?”“直播与我对观光景区的感受一样,其实都是一个虚空的理念。”
网路直播像是具有魔力的场域,现实生活平凡不过的人,也有机会在其中叱咤风云。“这也与我对观光景区的感受一样,其实都是一个虚空的理念。”张赞波补充道:“千百年来存在的自然景观,是如何被资本看中,再由资本跟权力合谋圈下来,去设计、包装、推出,最后吸引观光客过去,从而产生很大的经济效应。直播也是这样,一夜之间就能为看起来寻常的东西赋予一种价值。”景区与直播,两种吊诡的当代景观,刚好在柳静身上合二为一。
当张赞波带著疑问、也带著摄影器材来到内蒙古的乌兰布统,却有了更多意料之外的发现,其中一个就是徘徊在柳静身边的男人,书中称为郑总:“我原本是冲著柳静去的,却没想到她旁边还有这么一个男友,也隐隐知道他可能就是所谓‘背后的大哥’。”随著跟访渐渐深入,之后事态发展超出预料:本以为是慷慨金主的郑总,原来一直在“画大饼”;看似热闹欢腾的直播背后,也潜藏著数之不尽的人与人之间的算计、欲望、利益纠葛。这些散落在直播间外的砖瓦,张赞波一一拾起。

镜头穿过美好、对准残酷
摄影师们将相机对准了全新楼盘猛拍,而张赞波却深感不妥,因为他知道,宁县是当地出了名的“强拆之城”:“强拆那么严重,他们是本地人,他们都知道的。我还是个外来人呢。”
然而要进入圈子内部并不容易,遑论快速捕捉到这些因新兴直播产业而牵起的人际关系。张赞波过去在拍摄《大路朝天》时化身为“张赞”,白天参与到工程团队中、晚上偷偷剪素材;这一次,他依旧以张赞的身份,只是换上“帮忙拍摄宣传片”的角色,进入到陌生人的生活之中。问及如何做到这一切,他只答:“也不太好说是怎么来的,可能就是所谓的能量。”
“我对人物关系是很敏感的,这可能也多少跟我的电影训练有关,因为电影基本上就是在讲人物关系。”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班的张赞波,在学院里接受剧情片方法训练,其一是中心任务导向,拍出来的电影会比较模式化;另一种就是观察与呈现各种人物关系:“后来我讲课时也会说,没有中心任务,那就表现不同的人物关系,就会比较立体了。”
不同于剧情片,纪录片里没有提前设定好的关系,一切需要依靠临场感应。虽然张赞波称这种能力为“直觉”,但实际上也是需要累积而成:“例如郑总,一开始我也觉得他很慷慨、热情,他也总说‘我最喜欢蒙古人了’;但时间久了,就总会表现出来,藏不住的。”

虽是科班出生,自毕业以来,张赞波却从未拍过剧情片。而《大景》的前身,正是他第一部未完成的剧情片。
2017年,张赞波带著《风景》提案台湾金马创投。《风景》脱胎于导演一次在云南的见闻:“那里的风景确实很漂亮,像是上帝的调色盘。但是我们要进入到风景区之前,会经过一个很古老的大型矿区,里面全部挖空了,就像地震一样塌了。”张赞波留意到,面对如此残酷的风景,很多摄影师视若无睹,仅将镜头对准美丽的地方,“我想讲的是,他们无视这个真实的现实。”
在《大景》中,张赞波也写到另一次带给他相同感受的经历。湖南小城宁县的摄影家协会,常常举办或参与一些地方摄影比赛,其中有一场是为当地新建楼盘“爱琴湾”而设的有奖摄影大赛。在比赛中,摄影师们将相机对准了全新楼盘猛拍,而张赞波却深感不妥,因为他知道,宁县是当地出了名的“强拆之城”:“强拆那么严重,他们是本地人,他们都知道的。我还是个外来人呢。”事到如今,他依然忿忿不平。因此,当大家为了一个奖项而争相拍摄楼盘的美丽外观时,张赞波却选择“混”入驱赶钉子户的人群中,用DV记录下了糖衣包裹著的强拆事实。
“我知道,这样的场景,永远都不会进入这些在开幕式上热烈鼓掌的‘摄影家’们的镜头里。”这是他在书中为这场荒诞的摄影竞赛写下的注脚。盛事容不下的残酷风景,就装进张赞波的镜头之中。

在大历史中无处可逃
“有的人,他可能一方面家里正在受殃,同时又在说中国多富强。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些标语的作用,或者是这种意识形态宣导更加铺天盖地。”
后来,《风景》因为种种原因而搁置了。张赞波转而去内蒙古,到处逛:“就去看看那些观光景区嘛。”
起初,他要去的并非乌兰布统,而是位于锡林郭勒盟的“凤凰马场”,两地相距两百多公里。参访凤凰马场的经历,让张赞波感到十分神奇:“因为它是一个‘马文化’基地,又是刚好打著习近平提出的‘蒙古马精神’(的旗帜)而建起来的,这都是很吸引我的点。”来到这片边陲地带,他记录一路上所见的政治标语,在荒谬中默默观察:“这些空间看起来远离了权力中心,但是它总有一个办法来对应到权力。”
也是正是因为这些标语,张赞波的微博一度被“炸号”。
2018年前后,他曾在微博上发起一个征集行动,邀请网友发布在生活中看到的各种政治标语。整个行动过程,张赞波都在与审查机制斗智斗勇,尽管这些标语都是出自官方的政治宣传:“后来我都直接发布,一个评点也没有,甚至还要把图片倒过来,做各种处理。有时候能发出来,有时候不行。”
在与制度“死磕”的同时,他也留意著另一个民间对于这些标语的反应,似乎与网络上的挑衅与反抗态度完全不同:“有的人,他可能一方面家里正在受殃,同时又在说中国多富强。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些标语的作用,或者是这种意识形态宣导更加铺天盖地。”
张赞波关注的是人物,更是这些人背后的政治现实与历史。无论是过去的影像作品、还是文字之中,他常在纪实之外宕开一笔,将看似遥远的历史事件拉入文本。这一趋向在《大景》中更加明显。“历史是很重要的。处理一个议题的时候,除了横向的拓展之外,我也喜欢纵向,这其实从《天降》就开始了。”
《天降》讲述的是2008年北京奥运前后,中国大量发射火箭、卫星,碎片残骸掉落在湖南邵阳市的山村中,破坏农作物与房屋,更曾砸中一个女孩致使身亡。张赞波访问这些村民的同时,也循著线索,将一些被遗忘的历史事件搬到观众眼前:60年代广东汕头台风中的士兵牺牲、80年代原子弹爆炸实验后多人落下严重后遗症⋯⋯“其实主题都是一致的,就是为了国家发展、为了他们的官方的意志,人命不值钱。”
“‘皇家’这个词是非常核心的,民众对于皇帝,总是充满著对强权者的仰慕。”
十多年过去,在取材《大景》的途中,张赞波依旧感受到这片土地上,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无限拉扯。例如“皇家鹿苑”这个景区的名字,就触发了类似的感想:“‘皇家’这个词是非常核心的,民众对于皇帝,总是充满著对强权者的仰慕。”被命名为“皇家”的空间与现实政治空间对照,张赞波又忍不住搜集并补充了大量史料,将乌兰布统屠城之战等历史纳入书中,并列呈现:“有些人觉得我跑题了,但我觉得(从旁延伸历史)其实是挺好的,换句话说,会更厚重一些。”

自己成为自己的田野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是因为大家太听话了,他们才这么嚣张,最后什么法治、规矩都不跟你讲。”
《大景》有两片田野,一片是内蒙古草原景区和直播平台,张赞波在这里观察景区直播主和商人们的运作;而另一片田野,则是他自己。
早在前作《大路》中,张赞波就将自身调查的经验与感受在书中剖白;而到了这一本书,他更放开地写,写自己曾经遭遇过的电影审查、写微博被封书被扣押、写曾经在一个文艺营上意外记录下哀悼刘晓波的往事⋯⋯“写的时候我是有点犹豫,要不要把自己放那么多,会不会显得很自我?但后来我想,这些年时代的变化,其实在我身上都是有痕迹的,无论是我的遭遇,还是心理层面。”张赞波转念找到记录自我的意义,不再忌讳于他人的眼光:“因为像我这种身份的人,相对来说真是比较少。”
从事纪录片相关工作以来,张赞波一直都在与官方的审查体制、与极权体制作对抗。2016年,《大路》简中版被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责令下架;2019年,中国当局下令禁止中国电影及影人参与金马奖,张赞波在社群媒体上痛批“历史定会记住你们所做的一切”,而遭到中国网民连番举报。他把这些经历一一写进书里。
在原本的叙事架构中开一条岔路、讲述自己的经历,这或许会让一些读者感到疑惑。但张赞波愈写,愈是发现了这两片田野也有交汇点:“它们有种有机的联系,虽然可能看起来没那么明显。在柳静、郑总的身上,也可以感受到他们与极权的同构。”柳静、郑总等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为了流量,来去草原的新闻传媒也几乎都是官方喉舌,张赞波记录下这些众声喧哗:“新闻何为?艺术何为?利用新媒介的这些人,真的是只想吸引流量,而不去承担一点点社会责任。”他同时用自己的经历不断提醒读者——这片热闹图景的背后,有的并不是言论自由,而是无远弗届的审查与封禁。

然而,平台流量与官方的正能量,还是让愈来愈多人甘愿为之臣服。权力幻化成各种样貌,而它对个体产生的规训,到底能有多强烈?
这次来台,张赞波还带来两套短片《春山来客》、《春行即景》,正是为了反思规训而拍摄的作品。这两部短片可说是张赞波的行为艺术记录。在疫情期间,他买一套防护服,以及写有“疫情防控”的红袖章和扩音喇叭,摇身扮成“大白”,在寓居的山谷里到处宣讲防疫政策,不光对著人,还对著牛、对著花花草草、各种动物讲。“因为我成了政治的符号,‘大白’就是一个符号。”沿途有老人经过,张赞波扮演的“大白”手举喇叭凑近他身边宣讲,口中念出官方宣扬的口号“新冠病毒不可怕,只要大家听党话”云云,老人却沉默地听完,毫无抵触。这让张赞波深深反思:“要是有一个大白对著我这么讲,我会说:你讲那些恶心的话干嘛呀,防疫就防疫嘛,什么叫听党话?”
适逢清明假期,他还架起自称是“全世界最小的疫情监测站”,无论是居民还是路过的游客,都乖乖停下来做检查。一天十多个人,没有人提出过质疑:“无人质疑、无人反抗,就很可怕。”
这场实验,让张赞波意识到民众与权力的另一种关系,几近“合谋”。这也是他近年在许多场合反复提及的,关于“鸡蛋与高墙”间的辩证——在过去,张赞波总会站在鸡蛋那一方,然而经历了种种事情后,他却赫然发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是因为大家太听话了,他们才这么嚣张,最后什么法治、规矩都不跟你讲。”

镜头后的那人受伤了
“他们真的是对你也是利用,一点情感都没有。我想跟他们建立一种情感结构,根本就建立不起来,我觉得很失败。人性真是脆弱,因为他们的父辈也是这样,那样的环境里,小孩从小就这样。”
张赞波是在疫情前搬离北京的。
离开中心后,他经常寻找生存成本较低的乡郊住下,生活更加安静,也会在当地做些社会观察和田调:“我在现在住的地方,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年多,可能待足两年我又会换一个地方。”这种移动不定的生活型态,却让张赞波感到心安:“尤其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建立对这个地方的认知,这种过程其实很吸引我的,这可能也是人类学的一种方式吧,虽然我没有受过人类学的训练,但我很迷恋这样的过程。”
拨开表象,建立观察,最后浮现出一个结构性议题,这是记录者张赞波所热爱的事情。然而讲到这里,他锁了锁眉头,坦言道:“除了迷人之外,还有就是,对于‘人’这件事,我稍微有点受伤了⋯⋯”
拍摄纪录片多年,张赞波与一些受访对象常年持联络,其中就包括《大路朝天》中曾被现实体制重挫的挖桩民工老何。在后续交往中,老何常有“把日本人赶出去”一类的言论,张赞波却一直抱著谅解与共情:“观念不同并不会影响我们两个的交往,尤其我知道那是因为环境造成的,我也想试著跟他沟通。后来发现我们不但是观念不同,他有时候甚至为了维护强权而说一些假话,我就会很受不了。”

老何为了称颂人大代表制度,谎称自己也有份参与选举;不愿搀扶一下自己年迈的父亲,却把领导人说得比亲人更亲。诸此种种,都成了两人决裂的导火索:“一个对身边人都这么冷漠的人,他还维护强权,说得好像比他父亲还亲,我们要是讲(国家)的不好,他就跟你急。”
过去面对强权的阻挠威吓,张赞波总能愈战愈勇,为“站在鸡蛋这边”而反抗。老何的朋友面临强拆,他自愿提供办法、参与维权;留守儿童的家人不管不顾,他带小孩吃饭、给他们钱花。回过头来,鸡蛋原来已经与高墙共边站。老何不顾反对,在朋友面前无中生有,把自己说成是高干子弟;小孩拿著钱上了车,再也不回一条讯息。“他们真的是对你也是利用,一点情感都没有。我想跟他们建立一种情感结构,根本就建立不起来,我觉得很失败。人性真是脆弱,因为他们的父辈也是这样,在那样的环境里,小孩从小就这样。我真的很难受,因为之前我真是把他当朋友、当孩子。”
“有一阵子,我都天天躲在家里,根本不想出去,不想碰到这些人,不想跟他们再聊。”因为热爱,所以伤得更重,张赞波一时间失去了继续下去的动力:“我不做了,真的不做了。真的是伤了。以后我宁可写小说、写诗歌,不搞非虚构了。”
《大景》中柳静的个人简介令人印象深刻,她写:要想在狼群中生存,必先成为一匹狼。这个看似进取的生存法则,却多少透露出一种有违人性的时代精神,这正是让张赞波感到失望的原因:“在这个时代,人性也变得越来越卑劣。自己好像很努力去改变一些东西,但一点点改变都没有。”

电影没那么重要,书写还在继续
“人生它一直都在那,没完没了,只有死亡能划下句点。疫情来了,所有人都搅在里面,他们的命运改变很大。”
要问还有什么东西,能让受创的记录者仍然保有一点宽慰?在《大景》田调期间,内蒙古草原上的自然景观,曾令张赞波而感到震撼、动容:“你看著月亮升起来,真的是特别壮观,哪怕是在这种被污染的环境里,人造景观很多,但是我觉得自然的力量还是高于一切。”
张赞波的这次田野调查,总时长加起来一年有余;也是直至此次驻扎内蒙古草原,他才首次以观光客之外的视角来欣赏这片风景:“有时候你看到星空、看到月亮、自然的晚霞,幸好这些东西还没有被直播宇宙、被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给完全污染,这样的部分永远是在的。”
2020年初,张赞波暂别草原上的拍摄对象们,返回故乡过年,岂知疫情快速蔓延,计划不得不中断。这让人想起中国导演娄烨的新作《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当我们谈起这部电影,张赞波不禁感慨道:“而且我的这部还是两次‘未完成’,先是剧情片没有拍成,然后纪录片也被打断。”
在计划被打断以前,张赞波仍规划了不少行程,然而随著疫情愈拖愈久,最终无法实现。《大景》以拍摄对象们疫情后的生活转变作结,张赞波利用直播工具作为另一种田调方式,去跟进拍摄对象们的生活转变;从前很少使用微信的他,也为此特地开通“朋友圈”,试图了解这些曾短暂出现在同一片草原、最后四散各地的人们的近况。“结尾结到这,我是觉得够了。”既已成书,张赞波也对此释怀:“人生它一直都在那,没完没了,只有死亡能划下句点。疫情来了,所有人都搅在里面,他们的命运改变很大。所以我最后觉得,停在这也是天意吧。”
尽管计划已经收结,但经年累月在畸形的环境中拍摄,政治抑郁在所难免。从老何到郑总,还有更多这样的人事,一点一点加深了张赞波的创伤。那么,该如何继续下去呢?张赞波再次宣告:“就写虚构吧。”

“天无绝人之路。只要他们不限制我的自由,我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解决,许多媒介我都可以:写小说也可以,写诗也可以,或者不写也可以,去流浪也可以。”
拍了那么多年纪录片,真的放得下吗?他淡然回应:“以前在电影学院读书时,他们经常说‘电影梦’,比如什么‘电影梦的摇篮’,这也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广告词。好像在他们的眼中,全世界只有电影这种表现媒介了。我觉得其实不是这样的,电影没那么重要,你不能拍电影还可以做别的,可以书写啊。”
纪录片导演,或非虚构作家,这些身分并不能框限住张赞波。事实上,他也是如此“杂食”的读者,读博尔赫斯与卡尔维诺,读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的隐喻与节制,甚至他的第一部纪录片《天降》,也是源自马奎斯《百年孤寂》的魔幻写实与眼前现实的映照。“所以我向来都觉得,天无绝人之路。只要他们不限制我的自由,我可以通过很多方式来解决,许多媒介我都可以:写小说也可以,写诗也可以,或者不写也可以,去流浪也可以。”
“我不是那种非得要做什么的人,”张赞波已然非常了解自己:“之所以好像做了这么多年,也是因为反抗性使然——他们愈不让我做,我偏要做。他一旦要我做,我可能就觉得没意思了,哈哈。”
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未经端传媒编辑部授权,请勿转载或拷贝,否则即为侵权。